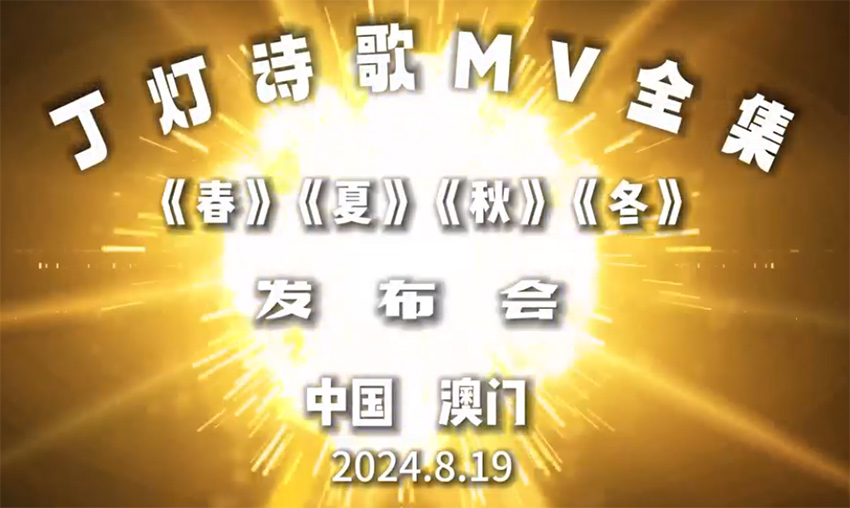故鄉:詩意地歌唱或傾訴
——讀王文軍詩集《洼子記》
作者:劉亞明
——讀王文軍詩集《洼子記》
作者:劉亞明
《洼子記》是我讀過王文軍詩集《凌河的午后》之后的又一本詩集。
那是6、7年前,王文軍在遼寧省朝陽市喀左縣的一個鎮當鎮長,我曾以《不老的鄉情——讀王文軍組詩<凌河的午后>》為題在《滿族文學》發表評論,認為:“如果從凌河的風土人情與詩意發現角度看,我熟知的詩人王文軍無疑是最為經典的”。而此刻,我又被《洼子記》所飽蘸的濃濃鄉土之情和清新質樸的詩風所吸引。看這部詩集名字,還沒有讀下去,我就執著地斷定洼子一定是王文軍的老家。這本集子名為《洼子記》,揭示了王文軍對洼子這方故土的深深眷戀和詩意感受。
關鍵詞之一:泥土中的血脈、根系和故土情結
王文軍這部詩集與其另一部詩集《凌河的午后》有異曲同工之處,主題都是有關家鄉、有關生活生命。朝陽喀左,是一塊神秘而詩意的土地。我們不能不說人生的某種必然,王文軍生在洼子,長在洼子,洼子的水土也養育了他的詩情和性靈。在王文軍的詩歌世界里,每一首都充滿了洼子濃郁的地域色彩。喝著凌河水長大的王文軍,從洼子土地上走出,正如一個人面對自己母親一樣,骨肉之情溢滿詩行,抒發了兒子對母親的敬意和深愛。
我注意到,王文軍這部詩集中那些來自山野的泥土氣息和故土洼子情結,清新質樸、理性張揚。一方面贊美大自然,把洼子看成血脈或根系一樣的土地;另一方面賦予泥土以生命,描述生活,記錄人生。詩集開卷詩歌《在這里,我愛》,有如詩集的引子,樸素與明亮的詩意一以貫之,和故鄉的子民一樣,仁人寬厚:
億萬年前從地下長出的山
神還創造了一條河流
蒼山不老,綠水也不老
這舊山河,養育著莊稼一樣的村民
田野上玉米、高粱是新鮮的
河里的小魚小蝦也是
……
在這里,我也和他們一樣
雖然很多時候
我的愿望和野心,像山一樣沉默
但這一點兒也不重要了
總有一天,命運給予我的愛
我會傳遞給別人,一個被愛原諒的人
罪與惡,也會被原諒
王文軍詩歌語言的鄉土氣息,口音一樣沒有改變,渾然天成,不是形式上的,更是內容和語言上的。那種純凈的鄉音,是“莊稼一樣的村民”所熟悉的,直爽真實,不是胡亂的東拉西扯,沒有虛情假意,更沒有當今詩壇上司空見慣的那種歇斯底里和玩世不恭。當然,最令人感動的是王文軍那些寫親情的詩章,他把土地與土地上的人或親情糅合在一起,血脈互通。在《清露無聲萬木中》(代序)中,王文軍寫道:“其實人的一生就像大地上的莊稼,熟了、割了、種了、收了,如此往復、歲歲年年”“母親不在了,家就不在了,而此時的家鄉叫做故鄉可能更為適合,它也許會無數次的出現在我的夢里,我卻會越來越少地出現在這里”。我想,王文軍以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作為自己這部詩集的序言,并申明會越來越少回故鄉,一定是用心良苦,隱含深意。無情的歲月、多情的土地、揮之不去的母愛……人生的經歷,是這樣一種人生歲月疊印的影像,一代又一代人的角色又在歲月更迭中完成了互換。而正是在這種疊印與互換中,王文軍清晰地看到人們生命的無可挽回的衰老和逝去,而更長久的是這片土地上的四季更迭、花開花落。這樣的詩歌記述,像一種恒定的軌跡,呈現出人生最深邃的親情與最溫馨的關愛。
王文軍詩歌里的畫面,有的質樸自然,有的憂傷沉靜。這些寫洼子的詩里有著宿命感和神秘感,更有著現實人生的在場感與堅定不變的信念。《老榆樹》在回首往事時盤點人生,再次談及生命本身就是一個秘密:“我猜過老榆樹的年齡,但猜不準/我爺爺小的時候/它就長在這里,就這么老”“從樹下走過的人/有的早已融化,成為泥土/有的走向遠方,長成樹”。在經歷了世事滄桑之后,一個心靈有所敬畏與信仰的詩人,內心良知尚存,世事消磨與歲月積淀一同醞釀,真實的詩意與人性的詩化一同打磨。《數親人》生動地記述了奶奶、母親和我的數親人,讓人感到王文軍詩歌是他多年在洼子生活中情感的生發:
每年春節,奶奶都會掰著指頭
數親人
簡單的加減法被她一遍遍重復
后來是母親,數著
增多和漸少的親人
講述被時間刪除的往事
平淡緩慢,像遙遠的記敘
現在我也開始數,為晚輩們
備好壓歲錢
為那些被我們親手埋進泥土里的親人
敬獻一份貢品和香火
活著的人和逝去的人
挨得那么近,他們都是一個個
繞不過去的數字
若干年后,后輩們
也會像我和我的先人一樣
把一些簡單至極的數字
數來數去,數來數去
王文軍詩歌語言,是他在洼子多年勞作、體察和感悟,以及一種源自生命性情與真實喜好的自然流露。在每年數親人的過程中,奶奶和母親先后把自己數了進去,“活著的人和逝去的人/挨得那么近,他們都是一個個/繞不過去的數字”的表述,有自然法則,精當而耐人尋味!但王文軍并沒有發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無奈感嘆,既為個體生命終將衰老而惋惜,也用詩性的語言、敘事性筆調寫出了自己的所見所聞。這首詩歌看似平靜的抒寫,有著來自心底感人的力量。事實上,對人物的描寫,表達了王文軍對人物命運和價值的思辨和評價,凸顯出現代社會背景中的個性歷史觀和人生觀。
關鍵詞之二:山村風景、地域元素與詩歌風格
詩歌,必定是對現實生活的外在反映。而一個創作意向,一個創作主題,總是體現著詩歌寫作者的審美能力。久居洼子,那一草一木不能不勾起王文軍的鄉音與愛戀。在王文軍詩歌里,山坡、山溝、梨花、杏花、槐花、山棗、玉米等成了專有名詞,作為他的鄉村詩歌的一種必備元素,成了王文軍詩歌在文學文體意義上的獨立與自覺。
我理解,王文軍詩歌中的山村風景、地域元素是其詩歌真實的復寫,是更形象、更生動、更精煉的語言藝術,是洼子特有韻律與意味的天然融合,是文字和圖像在讀者頭腦中浮現的雙重感知的藝術。一首《梨花雨》,讓喀左在我的印象中再次加深:
我堅信,這場雨
是為梨花下的
一滴雨,就可以
洗凈花瓣上的塵埃
這些天,山坡上
梨花肆無忌憚地開
追魂奪魄的白
運送成噸的芬芳
詩人李皓來喀左采風
正好遇上了這場雨,他說
“在遼西遇上一場雨,是小幸福”
我說,大幸福
就是遇上了梨花雨
我們在對王文軍詩歌解讀分析中,感受其風格特征,并對其作品中梨花元素作對應性解構和辨析,進一步了解其詩歌的多元結構,享受梨花本身所蘊含、傳遞的意義和意境。實事求是地講,一個人能寫詩不容易,能擁有自己的一本詩集更不易,但像王文軍工作和寫作兩不誤,一直堅持寫詩并成果頗豐的并不多見。我們所看到的這部詩集,已經遠遠超出世俗意義的本身,這樣的堅守是一種大幸福,就像遼西的梨花雨,更值得讓人擁有和動容。
毋庸諱言,洼子為王文軍詩歌的創作取材提供了極為豐厚的地域元素,但僅止于此是不夠的。這些山村風景、地域元素,如果沒有經過王文軍內在情緒的審視和恰當詞語的描述,是缺少詩意的。翻檢王文軍這部詩集可以看到,洼子的景致雖然有其地域性的特色,但其精神和意義往往又是超地域性的。王文軍選取洼子的人和事,就詩歌本質意義和哲學理性而言,更具有洼子的子民對生存狀態觀照和生活感悟的一般意義和普遍價值,更能引起讀者心靈的共鳴。同樣是春天,《春天是美好的》的表現手法,忠于內心并詩意表達正是詩歌的一種精神。這樣,不僅有一種通感畫面的呈現,更有意境方面的具象或意象。王文軍說:“如果是在山坡上,就應該有杏花/但你不要采摘,杏花這么美/更多的還是蓓蕾/沿著你走過的山路,入夜/小雨或者花香/會輕輕敲打你的夢//我也做夢/順著風/和小草一起綠到天上”。如此,王文軍的寫作風格非但沒有受到詩界詩風的影響,相反淋漓盡致地表現出其自身的人生態度和情緒體驗。
事實上,一個成熟的詩人一旦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后,便自然會在其詩歌中呈現和積淀出獨特的元素和符號。王文軍幾十年的創作生涯,有關洼子內容及題材最具故鄉的詩歌風格特征,可以說是對他詩歌風格的概括和肯定。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王文軍在洼子土地上進行了多重選擇,從藝術的角度,對各種詩歌與非詩的元素加以整合,把握了與自己的情緒相通、氣質相近,成為他感悟自我感悟人生的一種形式。他的《月色凌河》凸顯靜謐又不失浪漫:
月色皎潔了靜默
河水變成了白銀
就是一不小心踩碎了
也不擔心被魚兒咬傷
左岸,是我一個人的
右岸是麥苗鮮
蛙鼓蟲鳴,流水潺潺
似乎都在預說著豐年
遠山,近樹
竹籬,茅舍
還有幾聲犬吠
在月光的背影里
村莊,深邃如海
這個夏夜
只有我和凌河
享受著廊闊的月色
王文軍這部詩集多取材于洼子的山、洼子的水、洼子的風花雪月,詩歌的表達風格也在不斷地邁向沉實和成熟。換而言之,王文軍無論外界如何,依然堅守內心的寧靜,詩歌的內涵和厚度也隨著作者生活閱歷的增加而不斷擴展,筆下所描述的對象還是洼子土地上十分普通的事物,對人生對情感對詩歌的認識與理解,更加的透徹和單純。這些具有洼子特點的最普通最常見的人和事,具有真實純美的特點,反映了其創作追求的本體意義。
關鍵詞之三:鄉村敘事、生活記錄與樸素抒情
王文軍力圖以詩歌勾勒鮮活生動的“洼子風情”和村野氣息,契合了當下中國現代詩敘事化潮流。其一,平靜的敘事中有強烈的生命意識;其二,用豐富多樣的敘事手法記錄鄉情;其三,以親情展開詩歌人生敘事。詩集《洼子記》反映出王文軍詩歌創作的新變化,主要是在抒情詩敘事化方面做了可貴的嘗試。過去,王文軍詩歌大都很短,在這部詩集的眾多詩歌當中,題目為《洼子記》和《鄉居日記》的詩歌,格外的醒目,主要是這部180頁的詩集中,這兩首詩就分別占了35頁和20頁,足以見得王文軍對洼子的感情之深,不能不使他把這種情感化作詩的長篇。
在與詩集同題的詩歌《洼子記》的題記中,王文軍說:“村里人不關心上帝/只是一代一代地活著、愛著/并一再地死去”。如果說詩歌《洼子記》寫的是王文軍從出生到當下的詩歌記錄,還不如說是他迎著清新質樸的泥土氣息所展示的一種故鄉情結。在王文軍筆下,個人成長與洼子同步,他寫到自己的出生和受到的呵護,說出:“我曾踩著雨后的彩虹/奔跑,有人懷疑/我有隱形的翅膀”“老榆樹下的那眼老井/扔一塊石頭/就能砸出淘氣的童年”“村里人沒有時間/和花草交談/他們永遠忙于打撈光陰”等,也寫“山的那邊/一個嶄新的太陽正在分娩”“夏夜,坐在河邊納涼的人/聽青蛙和月亮一起/跳進河里濺起的水聲”“最長壽的人住在山坡上/他們和土親昵了一輩子/最后被土吃掉”等。這是一首有深厚文化傳承的鄉愁詩,從親情敘事角度看,王文軍詩歌更加日常生活化了,敘事抒情并重,增加了現實感、客觀性,達到了抽象抒情無法實現的感染力;從寫作手法上看,詩歌風格更樸素,言說更接地氣,結構更有動感之美和人性之光。
詩歌《鄉居日記》以奔放的激情躍然而出,勾畫出了一幅幅美麗的圖卷,信手拈來的鄉村場景隨詩句不斷涌出,深深感染著我們。從“村莊后面,有一條直通山頂的小路/每一次牽手這條曲徑/我都會慢下來、再慢下來/與沿途的花草、蜂蝶/交談言歡/感覺它們就是村莊里/我最熟稔的親人”,到“洼子,是我最早閱讀的自然圣經/村頭的那朵花微微一晃/我就讀出了她淡淡的憂傷”,再到“對這個生養我的小村莊/我是有愧的/這里有我的草木至親/如果不是再見/我也許就錯過了/村莊最深處的那一部分”,王文軍追懷并吟唱著給他心靈以陶冶與凈化的那淳樸、篤厚的洼子鄉風人情,這一切孕化為一種詩性的審美情懷,潛藏在王文軍的筆墨里。
在對上述兩首詩進行文本細讀后,我們不難發現王文軍詩歌創作出現了新的特點,在抒情詩中運用了敘事性手法,而且這種趨勢正在逐漸增強。從兩首詩意象的立體空間中,我們能夠體驗到熔鑄在字里行間的自由超脫的生命空間。這種以精神自由為指歸的境界追求,搭建著樸素的境界,一方面此境界反映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文化的一種滲透人文史哲的精神追求,是倫理、美學、價值、知識等諸多因素混合成的對生命的體驗與評價,另一方面是趨向于宗教與哲學之間的一種思緒或精神追求。有時,王文軍以一些具體的描述表達他的鄉村敘事和生活記錄,但他所真正要給讀者的絕不是具體翔實的描述,而是樸素的抒情以及精神層面的領悟。這種高度是王文軍通過詩歌創作所體現出來的思想、情感的高度,是詩歌藝術的高度,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人的生命高度。
王文軍詩歌將敘事、抒情于一體,無論是寫人還是記事, 在對現實素材進行藝術加工與重整的同時,都不忘敘事與抒情的緊密結合,以至于想象與寫實水乳交融、虛實相生、難以區分,讀來深摯感人。《祭祖》在敘事中的抒情,以親情展開詩歌人生,敘事富于聯想:“細小的火苗/眨眼間已躥得很高/很快就成了一堆灰燼/多像一個人匆匆忙忙的一生”。《大凌河》擬人的敘事與抒情的精短,具有強烈的生命意識。這樣的聯想同樣感人:
她瘦得只剩下骨架了
孱弱的水聲一步三搖
已經裝不下幾條嘰嘰喳喳的魚
我真想輕輕地抱起她
洗去她滿身的泥垢
讓她重新豐腴
真的抱起她
我就不敢再放下
我怕她也像逝去的母親
放下就再也見不到
她那枯瘦如柴的水聲
和當下許多中年寫作的詩人一樣,王文軍詩歌語言質樸平易、通俗流暢、不求華麗,以平靜多樣的敘事、動態的意象和擬人化的形象表現鄉愁,抒發著對母親的思念。王文軍這樣的詩歌敘事抒情意到筆隨,毫無矯揉造作,詩歌情節或細節為抒情提供基礎,抒情為敘事創造了更加深遠的空間,還如一個人的骨肉,相互依存。
關鍵詞之四:詩意的提煉、升華及現實主義的風格
榮格說,藝術說到底就是歸結為人格,無論藝術家有什么樣的思想嘗試,只有在找到可行的表達方式之后才能完整地呈現出來,這可行的表達方式就是藝術家品質與睿智的綜合體。王文軍在詩歌創作中注重寫實,注意從鄉村現實中發掘詩意,并加以提煉和升華,從而賦予洼子一種美的質感和濃郁的鄉土氣息。正是基于王文軍故土情結的內心驅使,使得這部詩集對洼子所構建的地域文化給予了現實的審視。
一首詩的誕生,絕不僅僅就是從起筆到收筆的創作過程,同時還與創作者的視野興趣、城府修養、審美思維、寫作技藝等分不開。這種藝術修養與每個人的學識、環境、經歷以及家庭狀況、社會背景分不開。所以,故鄉的描寫對于每個寫作者都應該是首選。那么,關鍵的關鍵是任何題材與體裁,如何去寫,如何走出平淡,通過提煉升華實現作品的與眾不同。我認為,王文軍詩歌的現實主義風格表現在,從素材取舍、主題立意、故事構圖、表現手法等各個環節的仔細斟酌。如,《那人就是我的母親》寫母親一生的節儉,從天黑收工回家著眼:
為了節省一根火柴
總是先點燈,再把柴禾
放到燈火上點著
……
日子摞著日子
補丁摞著補丁
在油鹽醬醋和雞蛋之間
來回換算
藝術來源于生活,但藝術不是完全的反映生活。對于上述我節選這些,現在的孩子們可能不知道不理解,但這樣的生活的確曾經真實地存在,相信從那時走過來的人,都會記憶猶新。這里,王文軍詩歌審美對象的外在感知能力、情感表現和象征意義不言而喻,體現出內在的精神與內在價值。這就如同繪畫一樣,通過物象體現自己的心境。每一節之后,“為全家人生火做飯的那個人/就是我的母親”“生育了三個兒子/也沒吃上三十枚雞蛋的那個人/就是我的母親”,這樣全文貫通的主題脈絡,可見王文軍具有十足的文字功夫,一方面考驗著他的審美感受能力、形象思維能力、創造表現能力,另一方面體現著他對藝術深層次的認識與理解。用對話描寫、行動描寫、肖像描寫、心理描寫等手段輔助敘事,進而,通過“一分一角地攢著/可還是攢不過清貧/多少年了/自己一根兒布絲也舍不得買/卻把兒女打扮得里外三新”,勾勒出不肯屈服于貧困的堅強的老母親形象。
詩歌寫作手段最終都服務于抒情。但詩歌的敘事性片段非常重要,它引發的詩性感情,是抒情的基礎,它使抒情落到實處,讀來生動具體,更為客觀,有助于詩歌情境的帶入。《梨花村》敘述中夾帶抒情:“嘴里只剩下一顆門牙的老太太/在花香里打盹兒/頑皮的孩子/把自己掛在樹椏上/露出的乳牙/比梨花還要白”。《一雙皮鞋》寫老白頭當兵轉業留在沈陽的兒子,回家過年給他買一雙皮鞋,他卻從未上過腳,不時地看,舍不得穿,揭示曾經的苦日子,讓人珍惜好生活。那時,這雙村里唯一的皮鞋也讓人有了驕傲的資本,“有人問起老白頭的皮鞋/他笑而不語/滿臉滿足的光/比放在柜子里的皮鞋還亮”。如此,王文軍詩歌主觀之意與客觀之象的交互與融合,通過可以感知的具象構建起詩的意境,呈現出簡潔、透明、樸素、恬淡等,具有極為現實的內在張力,以及審美性的哲學意味。
王文軍詩歌語言藝術的成熟運用和現實主義風格,摒棄了簡單的外在的表象描述,力圖在詩中融入深度的心理體驗,一如凌河岸邊的大豆與玉米一樣,彌漫著原野的氣息,閃耀著溫潤的光澤,萌發著生機勃勃的活力。現在,王文軍詩歌的視野更加開闊,詩歌的耕犁之鏵更加深邃與沉穩,詩中的意味更加醇厚而淡泊,內蘊深刻具有藝術審美價值,具備了這樣一種樸素與明亮的品質,已經成為自己獨特的語言基調。
結語
王文軍詩歌成績來源于他的勤奮和刻苦。
一個真正成熟的詩人是應該洗盡鉛華,細膩體察著人生,詠懷精神的故鄉,走進深遠。有鑒于詩人的本質,王文軍始終有一種對故鄉的敏感與熱愛,并且多年來對詩歌藝術孜孜不倦的求索。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東西在變。然而,王文軍詩集也真切地告訴我們,唯一不變的是不老的鄉情,是對洼子的掛念。詩人的職責就是留住記憶,從某種意義上說,王文軍有關洼子的詩歌就是一種挽留,也是一種堅守。他本著對詩歌對家鄉真實而堅定的愛,深情而專注地守望著洼子和凌河,守望著那里平凡普通的真實詩意,真實地記錄了故鄉的苦難史與生存史。
社會永遠比文字更深刻,生活永遠比作品更豐富。我以為,王文軍珍惜著生命中的滄桑、沉靜,以及傷感疼痛的心靈悸動,是對故鄉最好的歌唱與傾訴……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